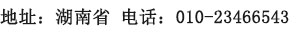大家好呀,马上过年啦!让小编为您解读文献吧!本期解读的文献是一篇于年6月发表的综述性研究,题目为“COVID-19andInflammatoryBowelDiseases:RiskAssessment,SharedMolecularPathways,andTherapeuticChallenges”
这篇文章的影响因子并不高,但里面的部分观点其实和我们的主流认识是相反的,这也让我们需要好好思考以下几个问题:
(1)IBD患者自身的炎症水平较高,是否可以预防COVID-19的感染?
(2)使用免疫抑制剂是否会影响COVID-19的感染机率?
(3)使用生物制剂是否会影响COVID-19的主要受体ACE2的表达,进而影响感染风险?
1
问题一:为什么IBD患者更容易受COVID-19的威胁?
我们已经知道IBD患者在感染方面的机率会增加,包括肺炎球菌,流感病毒感染以及其他感染并发症[1]。
IBD中目前使用的药物包括抗炎药(美沙拉嗪,皮质类固醇),免疫抑制剂(硫唑嘌呤,6-巯基嘌呤,甲氨蝶呤)和生物制剂(英夫利昔单抗和阿达木单抗-抗TNF,维多珠单抗-抗α4β7,乌司奴单抗-抗IL-12IL-23,Tocilizumab-抗IL-6R,Tofacitinib-抗JAK)。硫唑嘌呤/6-巯基嘌呤或免疫抑制剂联合治疗的IBD患者和50岁以上的患者表现出机会感染的风险增加。对抗肿瘤坏死因子(TNF)治疗与安慰剂进行比较的随机对照试验的荟萃分析发现,抗TNF治疗增加IBD患者机会感染的风险。维多珠单抗与呼吸道和肠道感染有关。结合当前疫情反复,入院可能增加感染风险。
乌司奴单抗使用便捷,注射方便,一年只需4次,且抗抗体产生率低,就目前而言应该是CD患者的最佳选择。
此外,最近的研究描述了与COVID-19相关的消化道症状(尤其是腹泻和腹痛)。另外,还有一例关于经内镜证实可导致急性出血性结肠炎并伴结肠损伤的SARS-CoV-2胃肠道感染的病例报道。
在重度COVID-19病例中更普遍存在诸如B型肝炎感染和肝损伤等消化系统疾病。冠状病毒通过血管紧张素转换酶2(ACE2)结合至靶细胞。可以在回肠,结肠和其他消化道部分,睾丸,肾脏,心血管和肺组织中发现ACE2的特别高表达。值得注意的是,研究表明,IBD患者肠道发炎与较高的ACE2表达有关,这可能有助于病毒进入。
最后,冠状病毒刺突蛋白与ACE2受体结合,是在宿主细胞表面发现的胰蛋白酶样蛋白酶的底物。胰蛋白酶样蛋白酶激活病毒刺突蛋白,从而启动病毒和宿主细胞之间的融合过程。已经发现几种粪便丝氨酸蛋白酶(包括胰蛋白酶样蛋白酶)增加了IBD的活性。
2
问题二:RWE数据与当前专家观点是什么样的?
虽然IBD患者容易感染新型冠状病毒的预期结果是基于可靠的推理,但现实似乎并不能证实。
当前数据并未显示IBD患者存在更高的感染风险,更严重的后果或疾病进程的显着差异。
一项基于人群的回顾性队列研究比较了名IBD感染COVID-19的患者和未感染IBD的患者,发现COVID-19严重程度的风险相似。
3
问题三:IBD患者的感染风险与正常人相似是否违反“常识”?
图IBD和SARS-CoV-2免疫病理之间的已知和可能的相互作用
3.1分子学机制。尽管SARS-CoV-2通过在IBD中表达更高的ACE2受体与细胞结合,但一项研究发现,结肠细胞中ACE2的表达与调节病毒感染,先天和细胞免疫的基因呈正相关,但与病毒转录,蛋白质翻译,体液免疫,吞噬作用和补体激活呈负相关。除表面结合的ACE2外,还有另一种游离形式的ACE2在血液中自由循环。已经显示出可溶性ACE2可以结合冠状病毒,与表面结合的ACE2竞争,从而防止病毒颗粒与细胞结合。研究表明,可溶性ACE2的活性在IBD中较高。这可能是IBD患者的保护因素。
CLEC4M编码的CDL是树突状细胞特异性ICAM-3捕获的非整联蛋白相关蛋白,已被描述为严重急性呼吸系统综合症冠状病毒(SARS-CoV)的替代受体。数据显示,CDL可以介导SARS-CoV感染,尽管程度不及ACE2。CDL在人肺的II型肺泡细胞上表达,但在肠道中也表达,两者都是冠状病毒感染的主要靶标。编码CDL的回肠CLEC4M被发现在克罗恩病(CD)中表达明显降低,提示CD患者可能对SARS-CoV-2具有保护作用。
冠状病毒和IBD之间的另一种分子相互作用可能与内质网(ER)应激有关。病原体以及自身免疫性疾病和炎性疾病均可诱发内质网应激,激活多种信号通路。响应内质网应激,真核翻译起始因子2(eIF2α)α亚基的磷酸化刺激了病毒蛋白。在SARS-CoV感染的细胞中发现磷酸化的eIF2α升高了四倍。相反,eIF2α在粘膜稳态中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,据报道,ER应激诱导的机制阻断了溃疡性结肠炎患者中eIF2α的磷酸化。
3.2治疗挑战。迄今为止尚不确定SARS-CoV-2是否由于局部病毒复制或随后的免疫系统反应而诱导严重病情的COVID-19。细胞因子和趋化因子的过度和延长反应,称为“细胞因子风暴”,由于免疫病理机制而导致较高的发病率和死亡率。TNF在“细胞因子风暴”免疫病理学中起关键作用。单核细胞巨噬细胞释放的TNF促进肺上皮和内皮细胞的凋亡,导致血管渗漏和肺泡水肿,从而导致缺氧。此外,由于T细胞在抑制过度活跃的先天免疫反应中起着重要作用,因此TNF介导的T细胞凋亡会导致过度的炎症反应。
冠状病毒特异性T细胞在病毒清除中也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。在一项研究中,TNF是唯一被中和的促炎细胞因子,小鼠受到SARS-CoV诱导的发病率和死亡率降低。值得注意的是,最近的研究表明抗TNF与COVID-19的风险显着增加或更严重的预后无关。因此,在COVID-19的情况下,IBD中的抗TNF治疗可能对患者有益。
乌司奴严重的机会感染率和结核病发生率很低,包括乙型/丙型肝炎病毒再激活。
用于IBD治疗的美沙拉嗪(一种抗炎药)和巯基嘌呤(一种硫代嘌呤)被确定为可用于SARS-CoV-2潜在治疗的假定药物。研究表明,硫嘌呤能够在体外抑制SARS-CoV和中东呼吸综合征冠状病毒的木瓜蛋白酶样蛋白酶。此外,一项全国范围的队列研究发现,硫嘌呤与COVID-19的风险增加无关。但是,由于临床研究表明可能存在肺毒性,因此在评估美沙拉嗪作为COVID-19的潜在药物时必须格外小心。
最后,尽管确定在IBD中使用皮质类固醇具有严重COVID-19的高风险,但一项研究表明,甲基强的松龙治疗可降低ARDS患者的死亡风险。在COVID-19中使用类固醇仍存在争议,必须谨慎解释可用数据。
总结
利用对SARS-CoV-2以及其他病原性冠状病毒免疫病理学的当前了解,证明了为什么IBD患者可能没有增加的感染风险或更严重的后果。但是,COVID-19是一种新型疾病,其作用机理可能与其他相关病原体不同,目前仍在研究中。当前的发现是否完全适用于IBD的SARS-CoV-2感染的发病机制,疾病易感性和治疗管理,还需要进一步探讨。
参考文献:
1.ClickB.,RegueiroM.Managingriskswithbiologics.CurrentGastroenterologyReports.;21(1):p.1.doi:10.
2.PopaIV,DiculescuM,MihaiC,Cijevschi-PrelipceanC,BurlacuA.COVID-19andInflammatoryBowelDiseases:RiskAssessment,SharedMolecularPathways,andTherapeuticChallenges.GastroenterolResPract.Jul10;:.doi:10.
预览时标签不可点收录于话题#个上一篇下一篇