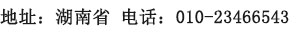罗某,男,48岁,军人。
初诊(年6月6日)胃部气闷作胀,不能坐下将近1个月。4月初因去沿海地区出差,多吃海鲜,出现便血,未加治疗。返沪途中自觉胃部不适,大便日行3次,左少腹部疼痛。回工作单位后,医务室给服黄连素片,但未能控制。因患者白细胞较低(3.9×l09/L),不能用氯霉素等抗生素治疗,医院内科,服用中药14剂,但仍无效,转来针灸。来诊时,患者腹痛,大便杂黏冻,日行2~3次,胃脘胀闷暖气,脉沉滑,舌苔白腻。此湿滞脾胃,复因多食海鲜油腻之物,再加乘船受凉,寒湿夹食,阻滞气机,传导之官失司而成本病。拟温中化湿,理气逐秽为法,针药兼施。
关元,天枢,合谷(双),太冲(双),脾俞(双),胃俞(双)。
平针法,关元加用温针,留针20分钟。
炒苍术9克,焦薏苡仁9克,焦茅术9克,青皮9克,陈皮9克,延胡索9克,川楝子9克,当归9克,紫苏梗9克,台乌药9克,香连丸4.5克(分吞),赤茯苓9克,泽泻12克,牛膝12克,生甘草6克。5剂。
三诊(年6月10日)针后脘腹闷胀稍舒,嗳气仍多,大便日行1次,黏液减少,脉沉滑,舌苔白根腻。阳明湿浊仍盛,再守上治。
上方加中脘,地机(双)。
同上。
苍术9克,茅术9克,薏苡仁9克,木香5克,台乌药9克,川楝子9克,陈皮5克,路路通9克,砂仁5克(后下),旋覆花9克,代赭石30克,香连丸4.5克(分吞)。7剂。
六诊(年6月16日)脘腹闷胀减少,大便日行1次,黏冻少许,头昏如蒙,多汗耳鸣,两肩关节酸痛,脉沉滑,舌苔白腻。湿浊内伤,上扰清空,侵犯表卫,脉络闭阻。再拟化浊顺气宣络为治。
公孙(双),内关(双),地机(双),足三里(双),中脘,气海,天枢(双),脾俞(双),胃俞(双),三焦俞(双)。
同前。中脘、气海加用温针,留针20分钟,背部穴不留针。
炒茅术9克,炒苍术9克,木香4.5克,台乌药9克,降香3克,川楝子9克,桂枝9克,干姜3克,淡附子9克,陈皮6克,泽泻9克,赤茯苓9克,白茯苓9克,车前子15克(包)。7剂。
九诊(年6月22日)6月18日做结肠镜检查示降结肠黏膜充血,水肿,血管紊乱,结肠袋消失。诊断为慢性结肠炎。针后嗳气、矢气增多,胀气明显减少,脘腹转舒,胃纳增加,两耳鸣响好转,但仍汗多怕冷。再守上方出入。
上方加上巨虚(双),天枢(双),外陵(双),水道(双),大巨(双)。
同上。
炒茅术9克,炒苍术9克,制半夏9克,炒枳壳6克,台乌药9克,川楝子9克,桂枝9克,干姜3克,附子9克,黄柏9克,陈皮6克,车前子15克,泽泻9克,生甘草9克。7剂。
十一诊(年6月26日)针药以来,矢气增多,大便已正常,脘腹胀气已舒松,胃纳转馨,冷汗已无,但今日上午左腹部又感疼痛,脉苔如上。守前治。
手三里(双),足三里(双),上巨虚(双),地机(双),内关(双),中脘,气海,天枢(双),外陵(双),水道(双)。
同上,腹部穴加用温针。
十三诊(年6月30日)针药以来,诸症明显好转,大便每日1次,无黏冻,无胀气,无不适感,胃口增加,精神良好,脉滑,苔薄白。再守上方投治。
取穴、手法同上。
炒茅术9克,制半夏9克,炒枳壳6克,木香4.5克,台乌药9克,川楝子9克,桂枝9克,干姜6克,附子9克,泽泻9克,赤茯苓9克,白茯苓9克,黄柏4.5克,车前子15克(包)。7剂。
十四诊(年7月2日)诸恙已失,脉苔如上。续巩固之。
手三里(双),足三里(双),内关(双),地机(双),中脘,天枢(双),气海,外陵(双),大巨(双)。
同上。
慢性结肠炎主要症状表现为腹痛、腹泻以及粪便中夹血、脓、黏液等物,类属于中医学中“肠澼”“注下”“下利”“滞下”“痢疾”等证候,并与各种腹泻症概称为“泄”。《素问·太阴阳明论篇》载:“食饮不节,起居不时者阴受之。阴受之则入五脏,入五脏则?满闭塞,下为飧泄,久为肠澼。”这种由饮食不节、起居不时、饮食与感染因素引起的急性腹泻,以后转变为慢性腹泻的载述,与本病的发病原因及过程类似。《素问·至真要大论篇》中则称“注下”,《金匮要略》中则称“下利”,“利”与“痢”通,故后代文献又称为“痢疾”,其有“下迫后重”之腹痛症状,粪少而黏滞,故宋代文献又称为“滞下”。其急性者,多兼脓血,可伴有发热,其病因金代刘完素指出:“大抵从风湿热论。”其慢性者,间发而久不愈,粪中多兼白色黏液,其因多属肝郁气滞、脾虚寒湿稽留而致,故前者亦称“热痢”,后者又名“冷痢”。本例患者当属“冷痢”范围,朱氏针对病因,拟从温中化湿、理气逐秽立法。取关元(小肠之募)加用温针,以起温复元阳、釜底助薪之功,用天枢(大肠募)以逐秽通肠;用合谷、太冲开四关以疏肝理气;取脾俞、胃俞以健脾和胃,引导清阳之气上升,浊阴之气下降。故诊后症情日减。6月16日诊时见头昏如蒙,多汗,耳鸣,关节酸痛,苔显白腻,朱氏辨为湿浊上扰,侵犯表卫,故加用公孙、内关以宽胸利膈,佐地机(脾郄)以化湿利水,用足三里、中脘和胃畅中,加三焦俞以运行三焦决渎之官,使水液之输布,谷物之传化得能各走其道。理法分明,施治得当,故此沉痼之疾,得获治愈。(本医案选自《陆瘦燕朱汝功针灸医案》)